
回乡下老家,带回来一个“钢灶子”。“钢灶子”是对便携式铸铁柴火灶的俗称,现在已不多见。
这个“钢灶子”闲置许久,锈迹斑斑,颇有些落寞的样子。尘封多时的物件,看上去都有这么点况味。比如乡村许多闲置的房子,建得漂亮,成色也新,但因为缺少人气的润泽,有点枯萎的感觉。房子的主人要么在城区购置了新居,要么外出打工,经年不回。
我把“钢灶子”安置在小小的后院里,用砂纸蘸水,细细打磨。年长的邻居见了微微一笑,说生锈的灶具 “服火不服水”,火烧除锈反倒要快很多。我半信半疑。家里有些现成的木柴,是前些年装修房子时的余料。我权且试试。
我引燃几根柴,把“钢灶子”侧倒在地,不断翻转,使其均匀受热。几次三番后,邻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扭成一团,让我使劲地擦灶体。果然,没多长时间,白铁皮做成的灶台就锃亮起来,铸铁灶体褪尽锈迹,有了红润的底色。
把“钢灶子”扶正,抓起一把枯竹条放进灶膛,点燃废纸引燃,接着放进去几根劈柴。
火在灶膛里燃烧起来,从星星之火到熊熊大火,仿佛一张笑脸在苏醒、在舒展、在腾跃。火与灶成了有机的生命体,在歌唱,在飞翔。火在灶里才有生命,灶在火里才是温暖。
灶台上坐上铁锅。火大,几秒钟的时间锅就烧“辣”了。菜籽油是从老家带来的,倒进锅里哗啦啦地响,就像田野里的雨声,有汪洋恣肆的野气。野藕带、南瓜藤也是老家带来的,下锅两分钟就炒好了。当我还是小学生时,每到这个时节,放学后就和小伙伴们打打闹闹,跑到堤边折野南瓜藤。那是农村孩子的劳动启蒙课,也是一种童年游戏。
几个菜炒好,开始煮饭。“大火煮粥,小火煨肉”,是母亲给我的真传。淘米下锅,添上几根硬柴,猛火噼里啪啦急烧,待水大开后,渐次减火,火的温厚浸过米饭,滋滋作响。虽然几十年没用柴火煮饭了,但我依然知道,一锅香透记忆和味蕾的锅巴饭已然完美成形。如果母亲还在世,一定会夸我的记性好。
我把这个“钢灶子”搬回家,是为了怀旧吗?或者,是因为柴火灶做出来的饭菜的确比天然气烧出来的好吃?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可资怀旧的东西有许多,用柴火煮饭也只是偶然为之。我想起乡下那些没人住的漂亮房子,房主人留下它们,现在是个念想,将来极有可能还是要回去的。有个实物在那儿放着,与故土隐秘而深切的联系就不会中断。
吃完饭,灶膛里余火还盛,于是搭上个铁三脚架煮茶。突然想到,就像“钢灶子”上的锈迹要用稻草才能擦去一样,擦去疲倦、压力、心尘,最好的工具也许就是能够连接纯真岁月与当下生活的“活”的器物。
(王宇,潜江市作协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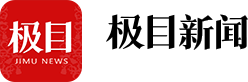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