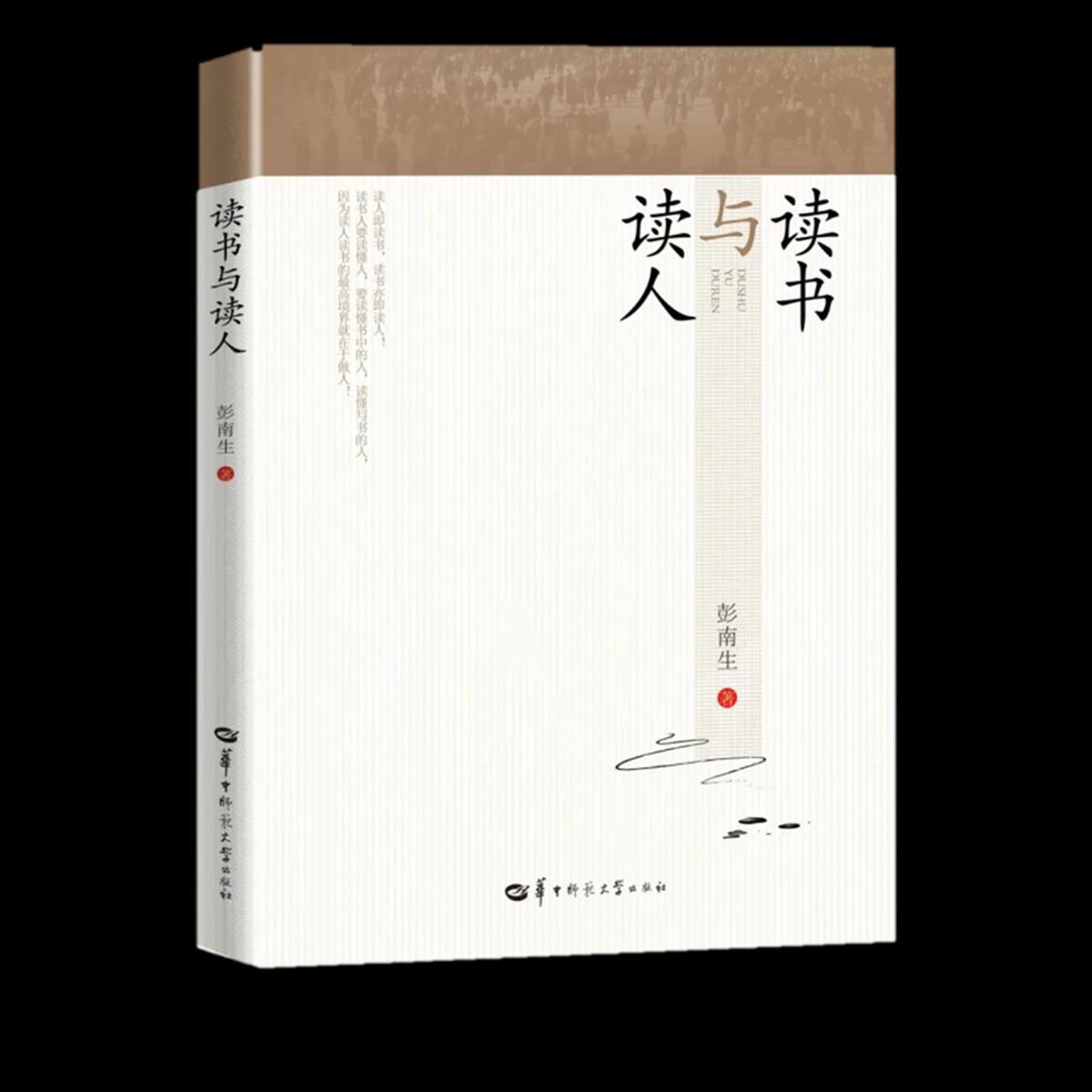
(一)
专家学者以研究学术见长,偶尔也会将自己闲暇之余的作品结集出版,虽然书名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均不乏随笔评论、随笔文论之类,书中内容无非是将自己做学问、谈读书、怀亲人、念故乡、忆师友、思历史、观现实的人生感悟及其经验心得,朴素浅白地昭告天下,让读者在一孔之见中斩获颇多。

彭南生教授所著《读书与读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就属于此类。书中辑录有随笔、文论、专访、序言,纵横捭阖,引经据典,有一种读岳南《南渡北归》那种大江大河的历史沧桑感。然,作者终归是学者,其文章遣词用字,准确平稳,缺少作家那种豪迈浪漫的排比句式,有的则是朴实无华的语言,看似平淡无奇,读之,发现作者讲究辞章之美,懂得笔墨的闲情趣味,且善于控制叙事的节奏。更重要的是其文章有见识,有思想,有情怀,同时重现实,接地气,精彩纷呈,爱不释手。
全书分为六部。第一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留校后在外地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再回到母校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作者回忆少年时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哪怕芝麻大点的细节都成为其性格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分量较重,是他对业师-----章开沅先生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史学思想综述。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留学还是访学归来,每位在海外“镀金”的学者,都会怀揣着西方某种思想话语,在国内大力推广。“章开沅先生多次表达了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洛赫的思想共鸣,尤其推崇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所担的‘使命’与‘天职’。布洛赫解释‘天职’,一是对史学的奉献;一是对社会的奉献。”这一史学观,是本书核心之要义。第三部是作者对教学改革的思考,或为理论探讨,或为经验总结,探索信息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之道。第四部围绕问学的经历与体验,是读者近距离地了解作者学术视野的不二法门。第五部是作者给学生写的序言,这些著作凝聚着弟子们的心血,也映衬着老师的史学观。第六部篇幅较小,是替友人作序,笔调显得有些匆促,作者谦称“勉为其难”,实则妙趣横生,他那明媚灿烂的文字,无论是品评历史,还是勾连现实,都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把控有度,而且贴近日常生活,阅读完序,迫不及待要看该书了。总之,这本随笔文论集,很适合刚踏入学术圈的年轻人,以及在学术圈迷失方向的读者,可以把这本书作为向导,迷茫焦虑时翻一翻,那种灵魂深处的共鸣,可能成为知己、成为好友、成为迷茫路上的指南针。
说起彭南生教授,人们往往想到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对其学术研究知之甚少。事实上,他是位历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著有《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等。
《读书与读人》书名来自其中的一篇随笔。作者认为,“只有读懂了他人,才能成就自己!”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彭南生在书中将此观点有所拓展。他说,“读书以观人,有良知的作者总是站在人类进步阶梯上,不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准确的认识,而且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智慧准确用文字表达出来。读这类书,更要读人,去感受作者的理性光辉。”(《读书与读人》)
作者正是通过读书,吸收前辈先贤间接的经验成长起来,成为他们村子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当然,他读书的时候也读人。他说:“母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家庭妇女,虽没有上过学,但却明事达理,是家里的主心骨。她与父亲在一些事情上常常相左,但在子女们读书这一点上,却出奇地一致。”“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虽未千叮咛、万嘱托,但行胜于言,给了我无形的、无穷的力量。”(《从木兰湖到桂子山》)
在书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他大学时代的几位恩师。
涂厚善老师的课如霏霏细雨,娓娓道来,他讲复杂的印度史总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他对印度种姓制度、佛教起源的分析,对佛教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关联阐释使我懂得了什么叫研究。(《我的大学岁月》)熊(铁基)老师在课堂上语速较快,富有激情,在我印象中,他讲稿用得不多,但板书较多,尤其是常常引经据典,并将关键的文献史料在黑板上板书出来,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属于研究型教学。但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我眼中的熊老师》
作者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近40年,对校风从不高谈阔论,而是让事实说话,平正通达而又富有说服力。比如,他写自己大二时,所在的班级组织了一场“为将满20岁的同学集体过一次生日,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请校长章开沅先生出席”。作者是组织者之一,居然冒昧地去“敲章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章先生”,“没想到,章先生答应了我们的邀请,我一时激动得手足无措,难以言状。”(《不逝的先生,永远的校长》)再比如,刘守华教授“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年逾古稀依然奔走在村村落落,街头巷尾,开展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故事,发表了大量民间故事研究的论著,编撰了多部民间故事作品集”。(《桂子山上夕阳红》)又比如,“吴(满珍)老师的课很受学生欢迎的,有学生回忆说,‘一般老师上课总要点名,而吴老师上课是不用点名的,因为教室里座无虚席’。她把上课看得比天大,对学生的指导也是极其严格的,有学生既感佩又惭愧地说:‘吴老师竟挑出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用词不准确和问题设置不合理等错误,当时的我既失落又敬佩。这符合吴老师的一贯作风——对学术求实细致,对学生严格耐心。’”(《师生情缘录·序》)
此外,书中还透露了他的业师——章开沅先生爱才、惜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轶事。“他(章开沅)在任校长期间,曾聘请一位园林科工人师傅为生物系讲师,这位师傅叫姚水印,他一辈子在华师绿化组工作,为华师园林绿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任校长前夕,章先生克服阻力将唐文权老师从苏州一所普通中学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后来他成为在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学者。章先生不仅是慧眼识才的伯乐,更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像姚水印师傅这样无学历和唐文权老师那样的低学历的人,能够被重用,充分体现了学校领导在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程度与唯才是举的胆识。”(《不逝的先生,永远的校长》)
大学是什么?作者没有浓墨重彩地写学习与探索,社会担当,厚德载物的涵养,以及独立的人格和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等。字里行间,却处处彰显这些人文底蕴,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他所在的大学格局之大,老师们像种子一样坚韧,破土而出,开花结果。
(二)
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马敏、桑兵、朱英、虞和平等章门弟子取得不菲的成就。作者在研究“章开沅的治学史道路与史学思想”时,转述了章开沅的观点:“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那么,“新的价值体系”又在哪里呢?章开沅似乎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走出中国历史近代史》第172-173页)
彭南生作为教授、博导,对学生要求不能像章先生那样宏观,他秉承“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职志。书中收录他不同时期的演讲,亦是其多年的治学经验之谈。他说:“学位论文题目,要么容易陷入泛泛而论,很难深入下去,要么因题目太过宏大,难以把握,让人不知从何下笔。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我认为关键是问题意识的培养。问题意识是一种敢于质疑的精神,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自觉,是一种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一句话,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问题意识就是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报告》)他注重研究前沿的“阵地意识”。他说,“一个好的选题要有可持续性。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需要考虑博士毕业后若干年研究课题的持续深入,占领一个学术根据地,使学术界同仁知道某某人在某个领域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同时也免得另起炉灶,这样较为省时、省力。一锤子买卖的选题不是一个好的选题,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费时费力,论文数量虽多,但学术界不一定知道我们的专长之所在。”(《在华中科技大学优博论坛上的演讲》)他认为,最初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方向、选题,就是选择自己的阵地。守住阵地,扩大阵地,这样的仗打的就更有意义了。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在史学界彭南生教授身体力行倡导“立德”在先,然后再“立功、立言”。在书中,作者不掠人之美,无论是转述恩师的观点,还是引用同门师兄的研究心得,他都严格标明出处,不据为己有。他的“立德”思想,与清代学者王念孙不同。王念孙为了避免掠人之美之嫌,凡知道自己文章中内容有与人相同之处,便一定将其删除。其在《读书杂志·史记序》言,他订正《史记》的讹脱,与钱大昕、梁玉绳说或同或异,因此在付刊时“凡所说与钱梁同者一从刊削”。作者则标明出处,并将他人与之相同的观点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与推广。
“学者随笔”是散文的一种体裁,是对有思想、有文化、有见地的教授、作家之作品的尊称。学者随笔,除了阅历、修养、人生境界与智慧,学问的底子也十分重要。老一辈有周作人、梁实秋、季羡林等大家,在他们的随笔里,更多的是从个人的阅历和生命感悟出发,忆童年,怀故乡,谈读书,悟人生,一觞一咏之中,多有喜怒哀乐之音,洒脱智慧之趣。彭南生与刘小枫、朱学勤、许纪霖等名家相比,其随笔较少探讨生与死、个体与制度、社会与政治等宏大问题,他的姿态更平实接地气,书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温度。譬如他写:“马敏教授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擅长宏观研究,他的论文常常体现出大格局、大气势,理论功底十分扎实。”“朱英教授则在论文结构、史料运用乃至遣词造句等细节上严格把关。”多年后,作者仍然感恩“导师的引领作用和导师组的集体指导使我受益良多”。(《将博士学位论文当作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
彭南生教授秉承的是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偶尔也通过大众媒体来宣传其学术观点。书中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报》和《长江日报》对其专访,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秉持的大历史观,引导读者从时空局限中跳出来,把过去放到现在来观察,把中国放到世界去比对,将历史置于一个无限延伸的坐标系中,使人们以古鉴今,探寻历史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共性问题。
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靠自己来决定,也只能全由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原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作者认同此观点,他说,“历史学更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积累,对现实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作者在思考、写作时,其立场、视角和兴趣,不可能超越个人所处的时代。但他认为,每一种学说远远不只是创立者所说的那些话语,这种话语本身是它在与别的话语斗争中,在它介入历史——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的新组合体。他要求学生,作为一名研究生,光挑选一种理论、一种话语、一种知识,据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是不够的,还得从原典中找其他材料加以佐证,支撑自己的研究结论。
作为读者,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给其硕士生、博士生写的序。在这些序言中,作者以介绍学生成果为主,极少提到自己,偶尔涉及,也是强调团队精神。譬如谷秀青是作者指导学生中第一个硕博连读的学生。作者在谷秀青所著《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序》中写道:“本来,我不赞成自己指导的硕士生继续报考我的博士,因为在我看来,理论上的修养、方法上的训练,通过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可完成,而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接受不同的风格的熏陶,博采众家之长,才能避免偏狭。好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和谐的研究氛围,对研究生也一向采取集体指导原则,在这个环境中,学生们既能听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高屋建瓴的学术报告,也能得到严昌洪、罗福惠、马敏、朱英等知名学者的指导。因此,六年来,她从一个略具史学背景的本科生,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开展研究的博士,这既得益于她的勤奋、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研究集体。”
作者这样写无非是告诫弟子,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才华,一定要在集体中,才能更大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华。特别是在学术界,合作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懂得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其他研究人员的专长和知识,不仅能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还能借助团队的力量推动了整个领域高质量的发展。其格局、其人品,与那些仅为蝇头小利者而言,像嵌在不同的历史地形中的,所处的岩层之间是无法比较的。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纵览全书,作者还记录了许多辛勤耕耘、不问报酬、不求闻达的俭朴的学者,退休之后,没有名利的羁绊,不受利禄的诱惑,自觉地扛起社会责任以及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道德担当。他们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对我们今天治史、治学仍有启示作用。
(彭四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学术著作《激励心理学》《寻找新闻的向度》《站在湖北看中国》,传记文学《永远的记忆——赵祖炳传》《记者穆青》。)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