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孤独》记录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的一次对谈。那时,拉美文学正处于“爆炸”盛况之中,对谈的双方都还是年轻的拉丁美洲小说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刚刚问世,而略萨凭借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获得了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
在这本书的译者侯健看来,现在的读者回过头再看他们五十多年前的谈话,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让自己“回归到1967年去,让那段不可复制的访谈体现‘在场’的历史价值”。
侯健主要研究拉美“文学爆炸”,尤重巴尔加斯·略萨研究,著译有多部相关著作,目前任西安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负责人。他对这场对谈的内容十分熟悉,因为在求学期间和工作后经常会重新阅读它,侯健对自己能够翻译这本“宝藏一般的小书”的经历感到十分奇妙。他认为“文学爆炸”让我们太关注四大主将了,从而忽略了拉美其他优秀作家和作品。
在1967年的这场访谈里,略萨和马尔克斯都还未提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文字的内涵”。侯健表示,这么多年里在中国语境下被树立起来的“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情况是否成立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澎湃新闻和侯健聊了聊《两种孤独》中提到的拉美文学关键词、如今的拉美文学,以及他最近的研究。
《两种孤独》书封
澎湃新闻:《两种孤独》的主要内容是拉美文学巨匠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唯一的一次对谈,对谈发生于1967年9月,主题是关于“拉丁美洲小说”。五十多年过去了,拉美和世界的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文学状况也与现在不同。对如今的读者来说,阅读这份文献时需要留意哪些变化?
侯健:我觉得在阅读这份文献时,我们首先要跳出“变化”的概念。因为正如您说的,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读者和拉美文学爱好者也成长了太多。我们也许读过许多马尔克斯和略萨的东西,不管是传记、访谈,还是视频材料,我记得2019年我去见略萨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你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作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问他们问题、看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谈话还有意义吗?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让自己回归到1967年去,让那段不可复制的访谈体现“在场”的历史价值。
举个例子,马尔克斯是个非常善于“扯淡”(这是作家的特长)的人,他甚至会在自传里描写历史事件时讲述一样模糊不清、从未被证实的情况(在他笔下,“波哥大动乱”发生时有一个煽动群众情绪的白衣人,完成任务后就消失了),也会在后来的许多访谈里扯淡。我觉得在做1967年的这场访谈时,虽然他已经在刻意地显露某些姿态了,但总体来看是很真诚的。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1967年的这场访谈里,略萨和马尔克斯都没有提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那么这么多年里在中国语境下被树立起来的“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情况是否成立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回归”之后,也许才谈得上“变化”,无论是对比后来拉美的政治变化,文学形势的变化,乃至两人私交的变化,都是后话了,这些话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历史化、在场化地去看待这场访谈,我认为书中除了访谈之外添加的文字(西语原版就是如此)并不是为了凑字数的,它们都是在引导和帮助我们回到1967年的现场,拿二十一世纪的目光居高临下地去看待这场访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澎湃新闻:人们谈到拉美文学时都会提到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写作风格是那个时期的拉美作家独有的吗?产生这类文学风格的土壤/原因是什么?
侯健:其实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也是个舶来品,没记错的话,这个词最早是在欧洲绘画领域出现的,在拉美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文学家应该是委内瑞拉的乌斯拉尔·彼特里。早在马尔克斯之前,危地马拉作家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和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曾经在法国留学,他们接触了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那些被欧洲人刻意追求的所谓的超现实的东西,在拉美很多时候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平常事,所以卡彭铁尔在《人间王国》的前言中说拉美的现实本身就是“神奇的现实”。
《人间王国》书封
关于拉美现实的神奇性,《两种孤独》里也有提及。不过这种神奇、幻想的特点并不是那个时期的拉美作家特有的。举个例子,拉美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就是本充满玄奇幻想的作品,当然我们还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我认为这些表征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有关,例如和万物有灵论的信仰、独特的死亡观等有紧密的联系。这些“神奇的现实”也是现实。还是那句话,“魔幻现实主义”在西班牙语里,“魔幻”是形容词,“现实”才是核心名词。我记得我前几天读到的南京大学张伟劼老师的访谈里他就提到了,现在我们要是说哪位拉美年轻作家是“魔幻现实主义”,他们会觉得在骂他们。所以是到了把拉美文学同魔幻现实主义剥离开来的时候了,因为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拉美的现实。
马尔克斯
澎湃新闻:“孤独”是这场对话的关键词之一,也在这本书的标题中出现。从现在往回看,可以说“孤独是马尔克斯作品的共有主题”吗?如何理解书中提到的一个评价:“孤独是拉美人的精神特质”?这本书取名《两种孤独》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侯健:我比较认同马尔克斯的看法,孤独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我不确定我们也好,欧洲人也好,有没有资格认定“孤独是拉美的精神特质”。昨天我做了一个挺火的性格测试,也许您也做过,里面有一道问题特别难选,二选一:在一周时间里,你更愿意只有你是快乐的,周围其他人全都不快乐,还是反过来,只有你不快乐,周围其他人都快乐。这其实也是种孤独感,哪怕你选择快乐,你仍然摆脱不了孤独。
到拉美文学的层面上,我觉得孤独是许多作家写作的主题,哪怕不是最主要的主题。我觉得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里主人公也是孤独的,略萨本人的《城市与狗》里的每个士官生都是孤独的,《酒吧长谈》也一样。不过,孤独在马尔克斯笔下有特殊的魔力,他对孤独有独到的理解,可能因为在老宅里度过的童年时代太刻骨铭心了,那个坐在角落椅子上一动都不敢动的小男孩一定是孤独的。所以我认为“孤独是马尔克斯作品的共有主题”是成立的,只不过可能这一主题在《百年孤独》及之前的作品中更突出一些。在《百年孤独》之后,我认为马尔克斯希望突破和改变自己,他之后的作品很不一样了,用略萨的话来说,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给自己“驱魔”了。
至于书名,没有官方的解释,我们也是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它,不过这也更好。西班牙语原版的书名就是这样,dossoledades,两种孤独。首先可能孤独本身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拉美文学乃至这场对谈的核心词之一。其次,文学家的创作生涯也是孤独的,他们面对白纸,只能自己帮助自己。成名前,他们蜗居在小房子里写作,孤独;成名后,到了聚光灯下,喧嚣之后,依然是孤独。
再次,我想起了关于马尔克斯和略萨的两个故事,有一次在接受访谈时,有人问马尔克斯这辈子是否失去过朋友,他伸出食指说道:“一个,只有一个”,而在《两种孤独》收录的略萨谈马尔克斯的文章最后,略萨说道:“当我发现突然之间我变成那一代作家里唯一在世的人,变成最后一个能以第一人称谈论那段经历的人,我很难过。”也许在一同在巴塞罗那度过的岁月里,他们曾经不孤独过,但是后来,随着友情的破裂,他们又重新陷入孤独。其实马尔克斯和略萨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政治理念、文学风格等等各方面很少有相似的地方,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人都是孤独的,是两种孤独,实际上也是无数种孤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澎湃新闻:这场对谈相当于一次“公开答疑”,本来主办方希望双方就小说创作、性格特征、私人经历等这些话题阐述观点,但略萨较少谈论自己,他更多的是向马尔克斯发问,他表现得很善于总结。比如,他在马尔克斯回答了《百年孤独》的创作细节后适时总结道:“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两项写作的固定要素了,……个人经历和文化经验。”您常年研究略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侯健:中文版出版之后,我看到了一些读者的评论,有一些读者说这次访谈“基本上是马尔克斯的独白”,我并不认可,因为提问者的工作实际上更难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里提出最关键的问题,引出答话人隐藏最深的东西,同时又要满足听众、读者的期待,既不能太浅又不能太深,这是非常难做的。但是略萨做得非常出色,一方面引导对谈流畅地进行下去,再一方面,我认为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表明立场的过程。
例如开场第一个问题:“作家有什么用?”略萨难道不知道作家的用处是什么吗?他当然知道。在那场对谈进行的一个月前,略萨刚刚在领取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的时候朗读了题为《文学是一团火》的演讲稿,在他看来,文学是武器,是一团可以烧尽愚昧、压迫、不公的火。他明白马尔克斯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所以他问这个问题。
您提到了略萨在访谈中进行的总结,他的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中文版今年或者明年就会上市了,您会看到他对马尔克斯作品的分析的脉络同他在那场访谈里对马尔克斯答语的总结非常相似。换句话说,他在1967年已经在引导马尔克斯按照自己画出的结构去作答了,我认为那场访谈实际上也是略萨对马尔克斯作品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成果展示。
至于略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近在Bilibili开设了“侯健的西语文学课”账号,第三期视频是讲我“追星”略萨的过程的,里面就提到了我眼中的略萨:为人随和,没有架子,非常有亲和力。不过在写文章时,在访谈中,尤其是涉及政治的话题时,他又会表现得非常犀利。
至于文学方面,在我看来,他除了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也是拉美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和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一起多引进些他的文论作品来,去年有《略萨谈博尔赫斯》,刚才还提到了《弑神者的历史》,后面还会有一些,我希望他写的关于福楼拜、雨果、骑士小说之类的作品也能早点引进过来。
澎湃新闻:拉美“文学爆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是作家的“爆炸”,还是读者的“爆炸”?除了“爆炸”四主将之外,那个时代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作家?
侯健:关于“文学爆炸”的起止时间没有明确的说法,一般认为它发生于1962年或1963年(《城市与狗》获简明丛书奖,《城市与狗》、《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跳房子》等“文学爆炸”代表作出版),结束于70年代初(作家们与古巴革命的关系发生变化)。
《城市与狗》书封
我觉得“爆炸”既是作家的“爆炸”,也是读者的“爆炸”,还是作品的“爆炸”,因为它们都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文学爆炸”本来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文学的角度看,拉美文学(小说)经过一百年的学习和积累,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从政治的角度看,古巴革命的胜利团结了拉美作家,增强了作家们的“拉丁美洲意识”;从出版的角度看,处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本土文学出版陷入瓶颈,给了拉美文学借西班牙的出版机构绽放光彩的机会,当然也要考虑到超级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塞尔斯、编辑卡洛斯·巴拉尔等人的个人努力,同时随着拉美城市化发展、文盲率降低,读者人群的增加,阅读水平也在提高……总之还是那句话,“文学爆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许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所以它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文学爆炸”的负面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太关注四大主将了,从而忽略了其他优秀作家和作品。例如轮流坐第五把交椅(何塞·多诺索语)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和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两位的许多名作这两年都在咱们国内再版了,我新译了萨瓦托的回忆录《终了之前》,另外他的《隧道》、《英雄与坟墓》、《毁灭者亚巴顿》,多诺索的《污秽的夜鸟》、《别墅》、《没有界限的地方》等都值得关注。另外古巴作家卡布雷拉·因凡特,他的“天书”《三只忧伤的老虎》已经出了中文版,另一位古巴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他的《天堂》非常出色,但因为作家本人一直低调而谨慎地居住在古巴,他的知名度一直没四大主将那么大。还有墨西哥作家埃莱娜·加罗,她的魔幻现实主义名作《未来的记忆》比《百年孤独》出版还要早,“文学爆炸”其实也有这种女性的声音,只不过国内外一直以来忽略了。
另外,今年我通过翻译和重读又更加巩固了我对另一位作家的看法,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虽然也贵为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但我觉得人们对他的关注还是不够,尤其是他的小说《短暂的生命》和《造船厂》,当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体验过挫折、失败、孤独和绝望之后再去读,感觉就太不一样了。值得关注的作家太多了,先说这几位吧。
澎湃新闻:马尔克斯关于每个拉美作家“都在试图描写现实的不同面……属于拉丁美洲的全景小说”这一说法,是不是提供了一种阅读拉美文学作品的方法?
侯健:是的,这也是“文学爆炸”一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大家不再各自为战了,拉丁美洲的整体意识更强了。之前在Bilibili做西语文学讲解视频时,也有朋友留言提问,想知道读拉美文学是不是要懂拉美历史。我记得我当时的回复是:要是哪部作品是必须拥有大量知识储备才能读的话,那它可能算不上是好的作品,但拥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后,我们阅读同一部作品的感受肯定不一样。
例如“文学爆炸”作家们,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的拉丁美洲意识,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关注拉丁美洲的历史、社会、政治情况,这些全都被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写到了作品里。我们从个体、家庭的角度看《百年孤独》是一种感觉,从哥伦比亚历史的角度看它又是另一种感觉,要是角度换成拉美视角、世界视角呢?肯定又不一样。
《霍乱时期的爱情》书封
就像很多读者差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因为男主角太渣,“作者三观不正”,这个视野就太狭隘了,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永远不能把故事的叙事者和写故事的作者等同起来,这是阅读小说的基础原则。如果我们从爱情的角度,从孤独的角度,从人生的角度,从其他更多样的角度去读《霍乱》,感受肯定又不同了。
再如我刚才提到的奥内蒂,我今年重新接触他的《造船厂》,我发现写得太好了,书里所有人都在伪装,都在演戏,不正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么?这是我在读大学时体会不到的东西。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如果能从拉丁美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爆炸”的作品,乃至把这些作品的作品放置到一起去玩味和思考,跳出某部作品,某个作家的限制,阅读的体验肯定会不一样。
澎湃新闻:“爆炸”一代作家为何受福克纳影响巨大?
侯健:这实际上是我曾经的博士论文候选题目之一,我当时想研究略萨对福克纳的接受,后来老师说这个选题欧美学者也可以做,所以建议我做略萨汉译方面的内容,于是没有做成。我想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爆炸”一代作家都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很多人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自愿流亡,他们对外国文学也持开放接受的态度。很多作家曾经说过,他们走出拉美正是为了更好地回头看拉美,事实是他们也真的能全面地理解了拉美。那么为什么是福克纳呢?当然了,对这一代作家产生巨大影响的不只有福克纳,还有海明威等作家,但福克纳一定在那份名单上,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批作家非常重视写作方法、写作技巧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这批作家最超越前人的特点之一。因为故事情节本身没有好坏之分,甚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精彩的小说,那么让这些情节变成好小说或坏小说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就是语言问题、技巧问题。所以写作技巧绝对不是在炫技,它是小说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两种孤独》里,马尔克斯就曾说过,拉美的现实本身就是神奇的,但是之前的拉美作家为何写不好拉美,因为他们总是想篡改拉美的现实,使之合理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阐释拉美的合适方法,所以他认为拉美作家们“得花功夫研究语言、写作技巧和形式,这样才好把拉丁美洲现实中所有奇幻的东西融入作品里,也才好让拉丁美洲的文学真正能够反映拉丁美洲的生活”,而语言和技巧方面的东西正是福克纳擅长的。略萨就曾说过,福克纳是他第一个在阅读时拿着笔,边阅读边写写画画,梳理结构的作家。我想这是福克纳对这批作家产生巨大影响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展现美国南部的社会百态,马尔克斯则以马孔多,奥内蒂以圣玛利亚,鲁尔福以科马拉来展现各自国家乃至拉美的社会百态,这也是一种学习,不过这也是技巧问题。
澎湃新闻:这场对谈后,两人再也没有同框?根据您的研究,两人为何决裂?
侯健:同框还是有的,而且不少。因为两人很快就在巴塞罗那当起了邻居,略萨为了写《弑神者的历史》肯定没少跟马尔克斯聊,两家人关系非常好,逢年过节一起过,这些内容在《“文学爆炸”亲历记》和《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记录比较多,但对谈活动确实仅此一场。
现在除了略萨一家,估计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决裂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双方都对此闭口不谈。我也(知趣地)从来不敢问略萨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揣测:一个是政治观念上的分歧。上世纪70年代初,古巴发生了要求诗人帕迪利亚做公开自我批评的事件,造成大批作家、知识分子与古巴革命政府决裂,略萨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略萨的政治立场逐渐右转(但是我和其他老师有过讨论,尽管略萨看重“自由”的概念,也许与传统自由主义关系密切,但是能否把他划到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是个存疑的问题,这里姑且不展开讨论),同时马尔克斯却反其道而行之,与古巴政府越走越近,同时拒绝在作家们的联名信上签字,诸如此类的事件必然造成双方的疏远。
但是略萨曾经断然否认二人的决裂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举了例子,他和许多人,例如乌拉圭作家贝内德蒂,有政治分歧,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也许还要提一下文学评论家安赫尔·拉玛,他和略萨虽然曾就《弑神者的历史》有过来回几场论战,但双方关系始终保持友好,拉玛不幸遭遇空难离世后,略萨还写过一篇感人的纪念文章)。
其次,生活方面,二人也有分歧。略萨非常注重社交礼仪,非常关注细节,但是马尔克斯在这方面则比较不羁。举个我翻译但还未出版的《巴尔加斯·略萨:写作之癖》中的例子:有一次,三位西班牙作家到略萨家中做客,他们想见见马尔克斯,于是略萨邀请了这位邻居,没想到马尔克斯穿着写作时习惯穿的工装和一双颜色不一样的袜子就来了,略萨当场就显得有些不快。但这也是小事。所以我认为,两人的决裂很可能还是私人生活方面出现了某些问题,很可能像传言说的那样与家中女眷有关,但说到这里,又不好妄加揣测了,我感觉这和当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的事件很相似,能激怒齐达内和略萨这样的“绅士”的大概只有家庭方面的事情了,纯属猜测。
澎湃新闻:当“爆炸”一代远去,中国读者上世纪80年代经历拉美文学阅读热潮之后,现在的拉美文坛有哪些值得译介的作家和作品?有何文学新动向?
侯健:“爆炸”一代远去了,不过拉美文学自“爆炸”一代起真正发展起来了,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已经难以动摇了,不管是所谓的“爆炸后”作家,还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还是70后、80后的新生代作家,都有重量级作品问世。而且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内对拉美文学的译介大有赶超上世纪80年代的势头,我甚至在我用西班牙语出版的专著《西语文学汉译史(1915-2020)》的尾声部分用了“西语文学汉译‘爆炸’”来形容西语文学近年来在我国的译介情况。大家读读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为《两种孤独》写序言《被寻回的文字》的哥伦比亚作家)、玛莉亚娜·恩里克斯、萨曼塔·施维柏林、瓦莱利娅·路易塞利等年轻作家的作品就能感觉到,拉美文学现在的新动向就是百花齐放,各种风格的作品井喷式出现,不仅有“爆炸”一代的宏大主题,也有更加细腻的故事,既有现实,还有幻想,也有恐怖,千姿百态,五光十色。
值得译介的作家和作品,老一代作家查漏补缺,也期待新译本的出现。例如上面提到的略萨的文论作品,奥内蒂的作品,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作品,埃莱娜·加罗的作品,莱萨玛·利马的作品等等。
至于年轻作家,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刚才提到的桑布拉和巴斯克斯,不过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的阅读量都是有限的,有很多好作品可能突然就出现了,也可能出人意料地就火了起来,例如去年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书封
澎湃新闻:您在译《两种孤独》时有哪些“aha时刻”(惊喜时刻)?除了这本新译作,您最近在研究什么?可以谈谈您的新课题《冷战背景下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前的进展吗?
侯健:“aha时刻”有很多,例如看到自己翻译过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两种孤独》里,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巴斯克斯,他写的那篇序言非常精彩,我译了他入选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废墟之形》,译本应该明年可以出版。还有刚才一直提到的《弑神者的历史》。另外,接受这个翻译任务本身也是“aha时刻”,因为这场访谈我在上学时、写博士论文时乃至工作后经常会重新阅读,不过西班牙语的纸质老版本我从来没找到过,后来西班牙出了新版本,我才终于买到,没想到最后变成了这本对我来说宝藏一般的小书的译者。这些体验都很奇妙。
我最近的工作安排确实非常紧凑,除了似乎永无停歇之时的翻译任务外,还要为7月份录制的文学课程写稿子,同时要完成学校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包括您提到的课题,“文学爆炸”这个课题我去年写了篇论文,然后就和很多青椒一样陷入了投稿-被拒稿-再投稿的悲惨循环中,我当时觉得应该跳脱出古巴革命这个小视角去看待“文学爆炸”,但一年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我觉得冷战的视角还是有些小了,这个问题我最近还在思考。另外我还在做教育部的一项课题,主题是“拉美文学汉译批评研究(1979-2022)”。
文学和翻译是我近些年做研究的两个重心或者说路径,我觉得国内对拉美文学汉译实践的关注很多,但是我们对拉美文学汉译批评的关注还太少,实际上翻译批评一方面可以丰富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来指导翻译实践,它还对创造良好的翻译环境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很多翻译批评依然停留在对词句、文本的对比评析上,但实际上翻译界早在上世纪就发生了“文化转向”,用句土话说,译者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进行翻译的,影响译者翻译的因素很复杂,评价译本的标准也是多样的,之前出现过一些翻译批评事件,有的有助于我们拓宽翻译思路,有的则大大伤害了译者、出版方乃至于普通读者,这就是恶劣的翻译事件了。所以我在对拉美文学汉译从1979年至今的翻译批评方面的东西进行整理和分析,希望能探索出一些东西来,为改善翻译环境做一点点小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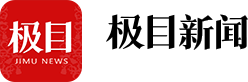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
鄂公安网安备 4201602000211号